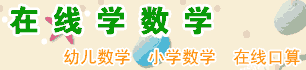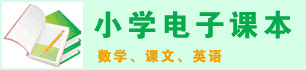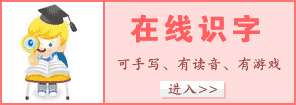������ˮ�껪�����߲����ֵ�ʱ�⣨11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ȵ�����Ϊͬ�顣�����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ǿ�ɥ���Ľ�ɫ���ð��źͱ�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ߡ�����ʾ�Լ��ı��ˣ�ֻ�е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¶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ɫʱ������ת��ͷȥ���ޣ���װ��û�п����ұ��˵����ӡ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Ҳ��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ͻ�ʹ���ջ�������ϲ�����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���ʹ����ͷ���ۻ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¡����ǣ������̸���Լ���һ����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ֱ�õ�Į�����࣬װ��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ӡ�“�����ĺ����”��˵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跨����ǰ�ߣ���ʹ��Ӧ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Ҳ�����跨�ܿ�Σ�ա�“�����ķ��ˣ�”���뵽��·��ɣ�ط���ʱ˵��“��֪���Լ��ĺ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ſ��ˣ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ټ������ͺ��ˣ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û��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ı����Ѿ��ϳ����أ�������Ŀȫ�ǡ�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˿���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ˮ���Կ������ũ���IJп�����ġ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˿������ʵ���ͬ���·��ɣ�ط��˵�ʹ�࣬�����е��ź����Dz�֪������ʹ���Ժ�����ʽ���֣�Ҳ���ܿ�������ʹ�ಢΪ֮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ҿ������ޣ�������ϰ��˵��“����Ҹж���”�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ع۲��ű��˵ĺۼ������ֿ���ʹ����̸���ޱ���ʱ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Į����ȷ�е�˵Ҳ���dz���ģ���ģ�ͬʱҲ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⻰——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ж���һЩ��ͷ��——�����ϵ�˵�����Ҷ��ٴ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㣺“�����еIJƲ�û��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Щ�Ʋ�������Ҳû�����ˡ�”�ܼ���˻��Ը�������˿˵���Ȼ�Ǽ������£���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ʿ������ʵ��ȣ�����㲻��ʲô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Σ��ܼ�û������Ԥ�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Ӹ�������˿��ʹ�࣬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ش����“ȷʵ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Щ����İ���ˣ���ʶ�����Ţ����Ǹ�����˼��”�ڿ����еõ���Ȥ�ĸ�������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“Ҫ�DZ���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ɵ�ע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”
����--------
������ԭ��Ϊgenss���Ǹ�������˿�ķ�������ӦΪgens�����ǣ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ս������ǰ�ܾã��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ض���˵��“Ŷ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̸�������Ǹ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�̵��ˡ�”���Ƿ��ڰ�ʾ���ڴ�֮ǰ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ָ�ƵĶ�ϰ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ֶ�ϰ��Σ���ԣ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**���ڴ���ǰ����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ĺ����ǣ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ͻ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ֲ�����ʥ¬�ͺ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ֿ���ԭ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뵽��δ��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ȫ�µĸо���һ�ּ����ǿ��µ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ڱ�Ҫʱ�������൱����ͱ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֤ʵ��Ԥ�е��Լ�����ز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Ԥ�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ܡ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ijЩ���ɡ����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ĸȥ���ú�������磬���ǵ���ŮҲ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Ͳ���֢֮һֱ�һ���꣬���ǵ���Ů��Ȼ�����Ҹ������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ɱ�����ֹ�������ڣ���һ�ֲ�ʹ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ֲ�ʹ���÷dz���ʱ��ʮ�����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к�����̵ĸ�Դ�����·���ֻ��ʹ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ʵ�ı�Ҫ��ʽ���ѵ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——����ʥ¬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ͬ���Ը�����ϵ��ԭ��Ҳ�����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һһ�о�——����Ҳ�ѱ�Ԥ�ȼ�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Ϊ���}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ͨ��һ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ʶ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ʶ�ı�����ʾ�������ں�һ������£�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ϵ������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Ѿ��ܿ�������ȷʵ�����IJ��ң������ֱ����Ǵ��б��˶��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֮�У�����ʹ�����ţ���ʹ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·��Ҳ�·����ǻ��ų��ļ��飬����Ц���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ͷ���а��۲��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˳�档�⽨�����ű���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鱻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̡���λ�Ƕ�â����ȥʱ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ȷ�е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Ա������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һ�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һλ�Ƕ�â�أ������ڹ�����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Ե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Ź��ź�ᣣ����ڱպϵĻ�Ȧ�£�û�����ֺ;�λ�Ŀ�ͷ��ĸ��ֻ�иǶ�â�ص�G�Ժ�ɫ���ֳ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ͨ�����ֱ�Ϊ�Ƕ�â�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У�������֮ǰ���Ҿ�д�Ÿ�ϣ�����ء���Ҳ��Ӧ�ø��Ƕ�â�ع�������д���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룬�����ޱ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ԣ������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ϵ�����ǵ������ֳ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룬�����иǶ�â�ؼ�����Ը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Ѫͳ��ϵ���ҵ�ʱ�����ѹ������Բ���д�Ÿ����е��ˡ��ҹ�ȥ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ޱ������మ�����罻����ʿ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మ��Ҳ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ǵ�ʱ�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⡣������Զ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ͺ�����ԥ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ʱ�е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˽��Ȥ�Ļ�����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ʹ����С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ʹ���Լ���һ��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æ������ʹ�����ⲻ�ҡ��ޱ����ط�Ħ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Ը�����Ƽ�����·ʥԼ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ֵ����ֶ���֤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ʾ�����ģ�ֻ��һ�ֲ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ı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ʮ�־��ȵػ�Ϥ�������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岻�ʣ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ò��ںü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ٵ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ڣ�����Щ����ʹ����Ϥ��һج�ĵı�ֽͨ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Ա�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ǣ��Ҹ��Ӿ��ȵ��ǣ��һ�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˿���һ���죬�ֲ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һ��˺ܳ�ʱ��——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Ǻܳ���ʱ��——�ŵ��Իָ������ҵ�֪����ʹ��ʱ���ұ��ж��ˡ�����ʹ��ʹ���е��˶���˵����Ҳ��϶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ꡣ���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Ϊ���Ѱ�æ�����ȱ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룬�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ʵ���㲻��ʲô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⣬�ڲ���֮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ʷ�ϸ�Ϊ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ʹ�ҵ��ĸ��ܸж�����·�Ƕ�â�ط��˵ı��ָ��ܲ��ñ��˵ĺøС���һ��ǵã����ڵ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Զ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ڳ���֮��Ҳһ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ͬ����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ָ��Ϊ��֪���ء��ڶ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Ҳ��ֻ����һ�˶���Щ���˺ʹ��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ս������ǰ����һ�꣬��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˷dz��ջ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ǰѱ���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ӻ���Ѷ�ɭ�������˳�Ϊ“������”�����ܶ�������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ڱ˵ñ��Ĵ�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⽻����“������”���⽻����罻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յ��Ƕ�â�ع������˷����ĵ籨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õ�����·������ܽ��Ů����Ϣ���ںܳ�ʱ�����λ�������ϵõ���ͬ�����Ψһ��ʾ��ֻ�����Ե�·�Ƕ�â�ط���һ�ˡ�
����ʥ¬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ǰ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£�����ı��˱ȹ������˵ı��˻�Ҫ����ʵ�����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Ǹ����ϵĵڶ��죬���о���Ī��˵“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”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죬ʥ¬Ϊ�ҵ�Ī�������еĻ���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Ľ����Ī��Ӧ�÷��۵��Ǹ����ӵĽ�����֪Ī�����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Ѱ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˶�ʥ¬����Ȥ���˼����ܵ��Ĵ�����ʥ¬��ʾǸ�⣬��д�Ÿ�ʥ¬�Ա������¸�������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ԭ���ǵ�· ����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“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”��仰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DZ��𣬾ͱ�ʾϣ���ҳ����ࡣ��˵��“���ǿ���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а·�����ѵ�ȫ���ҵĴ���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йص�·����˹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ͬ���ַ��ĵ�·�����ùŶ�������һЩ���£���ʵ˵��Щ���º�����û��ֱ�ӵĹ�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ͨ�����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ߵ�˫��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ģ����ʹ��·����˹�����͵�·�����ù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ʹ�࣬Ҳ��ҪС�����Ǹ��Ե�֪�Է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ֱ��֪������ʵʱ��ʹ�࣬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д���ĬĬ���š�ƽƽ�����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Ǻܿ�ͱ��ͷš�Ī��Ҳ����ˣ���Ϊ����д��ʥ¬�������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“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ս����”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Щ�£���ֻ�ǰ�Ī���͵�ǰ�ߣ�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¸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Σ�գ�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ʮ�־����»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öʮ�־����£���·����˹������ǰ��ͽ�͵�Ϊ�����飬ʥ¬���ӵ�Ϊ�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Ӵ�֮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ö��ʧ�����Ȱ��Ƕ���ʮ�־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Ҿ������룬Ҫ��ʥ¬�����ţ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ٵ���ս����е�ѡ���б�ѡΪ��Ա��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ĭ�������Ĺ�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͵�ƫ������ս����ʧȥһ����ָ���˿���ͨ����ɫ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ͥ�����ʮ�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ڲ�ı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õģ�������ʹ��ͨ��ʤ����ѡ�ٽ�������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ѧԺ��ʥ¬������“��ʥ��”���壬���ĵ�ѡ�ͻ�ʹ���ٶ�·÷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īˮ��Ȫˮһ��ӿ�������ǣ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İ�������ֿ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ȡ�����ѡ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˼�롣��Ȼ����ЩӢ���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ǣ����ڹ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Щ�ϻ쵰Ҳ�����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ٴε�ѡ����Щδ�ܽ������Ա��Ժ���ϻ쵰�����ٵý��뷨����ѧԺ���Ͱ���Ԫ˧�ǡ�������ͳ������Ժ�鳤���˵�ѡƱ����Щ�ϻ쵰�Dz�����ʥ¬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Ȱ�����һλ���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ֵ�������ٴε�ѡ����Ȼս�����ѽ�������ȴ��Ȼ���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ٵľ�װ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ѡ��ʾ���˵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б�ֽ���й�����˺�ԣ��Ůʿ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ƾɵ��·��dz�����ںͺ��¾�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ʿ�Ϲ�����ʯ���Ⲣ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ǵ����ӣ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ʧȥ�˶��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Σ��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ŵIJƲ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ʹ�ȶ���Ʊ������һǧ���ɡ���ô��Ĵ���ʹ�˸е��е㲻�죬�����ǶԹ������˵ı�Թ�������٣���Ϊ����ͻȻ�����˲���ʲ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Ʒ��һЩ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ڣ����ǵ��ɷ�ɱ�������ֳ�����ǵĶ���û�гԵģ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ʯ�飬�����ڳ������б����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ӵ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Ⱦ�������ߣ��ᴫ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Щ�������ѵ���ͻȻ����¶��……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ס�����Ǽ�����Ժ�����β�����Ч�������ȵ�һ������Ժ�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Ҳ��뿪�������Ժ�����ڳ˻ذ����;�У��뵽�Լ�û����ѧ���ܣ����ҹ�ȥ�ڸǶ�â���DZ�ȴ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ֲ��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ǰ�ö�ʱ�䣬�ڻص���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ǰ��ÿ��ͬϣ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ɢ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ʶ������û����ѧ���ܵ��뷨�����뿪�����ص�ǰϦ�������Ķ����Ŷ��ֵܵļ�ҳ�ռ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뷨ͬ�����ĺ���ѧ����ƭ�Ե�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뷨Ҳ������ʹ�࣬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Ҹ������Ŀ��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ŵ����벢�����ڣ������뷨���кܾ�û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֣�����ȴ����ʹ�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һ�ִ�δ�й��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Ҽǵ������ڻ�ͣ�����µ�ʱ������һֱ�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ĵط������룺“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ɶ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ڴ���Ȼ֮�У���ĩ���ҵ��۾�����Į�������ĵؿ������Ƿ��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ķֽ��ߡ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Ϊ�Լ���ʫ�ˣ���ĩ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ʫ�ˡ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ʼ���ѿݽߵ��µIJ���֮�У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ḳ���Ҵ���Ȼ���ٸ����ҵ���ʾ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ܶԴ���Ȼ����ک�����Щ����Ѿ�һȥ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”���ǣ�����Ȼ�ÿ��ܶ��˽��еĹ۲�ȡ�������ܵõ�����ʾ�������ο�Լ���ȴ֪���Լ�Ѱ����Ǹ��Լ�һ�ְ�ο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Ҳ֪�����ְ�ο����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꣬�����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ǰ���ڱ����ϼ���һ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̤��߶ȵ���ЩС����ǰ���ҽ���е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ЩС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ǵ���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д�úõ���ȴ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Ƿ���ָ���Ѷ���û�ио�������Ȥ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أ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ͬ������Į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ӵĴ������н�ɫ�ͳ�ɫ�I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ҿ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ӷ·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൱���ص�õ�����Ͻ���ġ����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Щ��ͬ�ķ��ֶ�������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ͬһλŮʿһ��ɢ��ʱ�ҿ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Ƭ������Զ���ֿ���һ��ͬ����ʯ��µ�һ�����ʹ��ɵ����壬���Dz�ͬѰ������ɫ������ʹ�Ұ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ɵķ��գ����dz��ڶ���λŮʿ����ò��Ϊ��˵Щ����ҲΪ�˱�ʾ���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ɫ���Ҿ���·��ʱָ��ָ��Ƭ��ɫ�������ǿ�´���ʯ��ë���Ρ�ͬ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Ҷ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���ܻ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еõ����Ҹ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ָ���˲������ϻ�һ��ķ���ͷ��ӱ�Ĩ������õ���ɫ�����ǣ�ͨ���Ҷ�������Щ����ӡ���ͬ�飬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־������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飬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Щ��ɫʱû���κ�ϲ�á�
�����ҳ��ڲ��ڰ��裬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ǵ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Ĺ����ظ��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Щ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Ů����Ů���ٰ�IJ�㣬��һ���ǵڶ����ڸǶ�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����ۻᡣ���ڻ��Ͻ��еı��˵�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Ǵ�ʹ��ȥ�μӾ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ԭ��֮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룬�����罻����ʿ������ȷʵû�б�Ҫ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ÿ�춼ϣ���ڵڶ��쿪ʼ������˲����“����”���Ҳ��ʺ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ʺ�ȥ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κ���ʵ����ʵ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����ģ�ֻ��ʹ��Щ����ʹ�Ҳ�ȥ�μ�����罻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ʧȥ��ֵ�����ǣ���ʹ��ȥ�μӾۻ��ԭ���ǸǶ�â������գ����൱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ֱ���ҵ��Ժ�֮�⣬���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¾������ڹ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壬��ʱ���ڻؼ�;��·����֣������濴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л��һ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Ƕ�â����ү�IJʻ沣������һʱ�䣬�Ƕ�â�ؼ���ij�Ա��ʹ�Ҹе����罻����ʿ��ȫ��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⣬���κλ��ŵ��˶������⣬��ʹ�Ǿ���Ҳ����ˣ���Щ�˳����Ҷȹ�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й������д���ζ����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ڳ���С�ֵIJʻ沣�����Ͽ����Ĺ�ȥ������Ҫǰ���Ƕ�â�ظ�ۡ���·���Ӧ��ʹ�ҽӽ��ҵ�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п���ͯ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Ҽ����ض�������ֱ����Щ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ص��յ���ĸ�����췴����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ȡ���Լ��Ķ����ԣ�����ƣ����۾�ǰ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һ���Ҳ�֪�������ơ���
����--------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ʿ�����˼ҳԲ�㣬�����Ⱦ�֪������ۻ�ʮ�ַ�ζ�������ҾͿ��Ժ��˼ɵ�ǰ���Ƕ�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ĸ�ۡ��——����ע��
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Ա�ǰ���Ƕ�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ס���Ѳ��ǹ�ȥ�ĸ�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ڲ�����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ۡ���罻����ʿ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ǣ����ȵ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Ҫ�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——��ʹ��֪����ʵǡǡ�෴——�Ƕ�â�ؼ�����ݼ̳�Ȩס��i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ʦ����Ů�Ĺ������Щ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·�ͻ�ͬ��ʦ����Ů̸��һ�����ѡ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û��ʲô�±ȱ���ʹ�����Ÿ������ף�������ǰһ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ʳƷ�ӻ����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д����ǰ��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Щ���˵Ķ��ӡ����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ķ�Ƕ�������Ф��֮Ϊ�����ǵ�Ф�����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ת�ã����䲻�ָܷ���ڸǶ�â�������ᵽ������־�ס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ѱ���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ͨ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ҵ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컨�壬���汾Ӧ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յ������;�η������ȴ�ӻ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Ȥ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Ů�˵�ҹ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Ǹ������ǵģ�i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˿�վ�ڲ�����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ǰ�棬��ػ����ҹ�ȥ�ڸǶ�â�������ɹ���ǰ��ʱ�����ĸ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䣬�����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䣬������ʧ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ʮ��ʱ����ʧȥ�˶�ͯ�������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ɷ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˳�����Ϊ�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ţ�̣�����ͯȴ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ţ�̡��Ƕ�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ض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i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Щ�뷨�ij������봩����Щ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ֵĽֵ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Щ�ֵ�·��ܲ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Щ�ֵ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ر�����ĸ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ָо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ڳ�ͻȻ���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绨��դ���Ŵ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ߵ�����ϸɳ���Ҷ��С�����棻��ʵ�ϲ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ͻȻ�е�������ϰ�������ʧ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Ҳû����Ӧ��ע���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ڲ�֪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ʵ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Ľ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ҹ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˿һ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߹��Ľֵ�����Щ�ֵ����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汾�ܵ�֪��Ӧ��ͨ��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ͱ��˷����Ҿ���һ���ڴ�֮ǰһֱ�ڵ�������ػ��еķ���ԱͻȻ“���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߿ա��ڰ��裬��Щ�ֵ�����Զ��һ�ֺ������ֵ���ͬ�I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չ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ҽֵĽֽǣ������ȥ�и�¶���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˿ϲ������Ƭ����ʱ���Ҹ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ٸ��Ŵ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ţ�ֻ����ԭ��ת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IJ��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Ľֵ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滬�����˺�����Ĺ�ȥ�����⣬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˶ͬ�Ĺ�ȥ��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˸����Կ��壬�����˸�����Ϊӭ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ķ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߽�ijһ�����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ѺͰ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Ϊһ����·�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ĺ��壬����·�������߹�һǧ�Σ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ֲ�����ά����ȥ��Ҳû�е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緹���߹�������·���ҵ�ʱ��˴�æ������˷ܵر��ܣ���Ϊ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δ�ɵ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͡�����ñ�ĺ�ɫ���ۡ��ٵ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ҶԸǶ�â�ظ����е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ͷ����β�������Ҿ��ó�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³�������ȴ����ؿ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ͣ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۷������ձ���˵���ڳ������ŵ�����˵�Ƿ������棬��Ϊ����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Ŭ��һ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--------
�����١�����ñ�ĺ�ɫ���ۡ���1837���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Ұ�˹����·�±���1782—1871������Ļϲ��磬Ҳ������ɹ��ĸ��֮һ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ǣ����IJ�ñ��¶����ȫ���ס������Ʒ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ͷ�������°��ϳ����İ��Ӿ���ѩ�ڹ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ĺ��ӡ�ֻ�����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æ����ͣ�������˾��ǵ�·����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з�֮�����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֪�����ù��з磨��ֻ����˵���۾�Ϲ�ˣ�Ȼ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ʱ���Ӿ��ϰ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ܿ���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ڴ�֮ǰȾ�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˽�ֹ������ƣ��Ⱦ�������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ֻ�ѧ������ʹ�������ɴ������ɵ�һ��ͷ���ͺ��ӣ���ͬһ������Ъ����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ѱ��͵Ľ�������ʹ������Щ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Զ�������ʶ�Ŀ�����һ�ǿ�а�ɯʿ����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λʧ�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۾���δ����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ԵĶ��Һ�ұ���ʱ�֮�⣬������һ�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ʧȥȫ���Ĺ�ʡ����ǣ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ǣ����Ǹе�����ʧȥ�Ĺ���Ǿ����ϵ��Ժ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ˣ���· ����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ڹ�����Ժ�����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ڣ�������һʱ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Ժ��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һ�塣��ʱ����·ʥ�·Ѷ��ط��˳����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ȥ�Ƕ�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о�����Ϊ��λ���˶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Ư�������Ȱ����չ�С��һ���չ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ߵ���˵���Ǹ����ˣ��ǵ�·ʥ�·Ѷ��ط��ˡ���·����˹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ϣ����ʾ�Լ�����ɶ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ѵ����ж����I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ѵ���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ñ�Ϲ������· ʥ�·Ѷ��ش������⣬���ij̶Ⱦ������Ƿ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㡣�ڵ�·����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֮�У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µ�ԭ����֪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ܸж����ˣ���Ϊ���ֶԲ�����˵ʹ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ֺã���Ϊ�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̾����Ϊ�Ľ����߸е����ˣ��ɼ������Ƕ���ڵĿ�����ͬ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о��Ķ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ʹ��Ե��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˶�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Ķ�����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Ҵ��п����IJ���˵��һ�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ᣬһ�ֶ�������ʵ�ij��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ͳ�������Щ�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Ӱ���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ϳ����Ƿd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ġ�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¶����ʾ�ı仯��û���罻������ʶ��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̣�����ǫ���ߵ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ϵ���ڵ�·ʥ�·Ѷ��ط�����ǰ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Ů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ʹ���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ڣ������ڴ���ǰ��ʹ�õ���ڣ���ǰ��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ŵĹ������ű��ǫ�����о�һֱ�����һֱ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δ��Ӱ�졣�о��Ե�·ʥ�·Ѷ��ط������ڶ���ǫ�������⣬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˹��ij���ϳ��ӿ��ܶµ���˹��ѹ�ֵ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ۣ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κε��ʣ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ٻ������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н����Ǻε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־á���·����˹�����ڴ�֮ǰ����ͬ��͵�·ʥ�·Ѷ��ط��˹������ͣ�����ȴ����һ�Ϲ����ס��ٽ��ܵ�·����˹�����ľ��⣬������˵ȫ�ǹ������ţ������о���ȥ�ܾ�������ʾ����Ҳȫ�ǹ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·����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ʹ��·ʥ�·Ѷ��ط�����λ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ı��ԣ�ȴ�����ý���װ�������Ӻ�����ñʱ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ӻ�Ϊ���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ڹ������Բ��𰣢ڰ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ñ�ӵ�ȫ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ĺ�����ñ�ӵ���ӿ�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Ȱ������о����˳����Ҷ��о��й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ٶȺܿ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ô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Ļ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ظ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ͷ������ƣ���ʹ�Ҹе����ȵ��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ڿ�ʼʱ���ޱ��飬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̱����֢״�����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ҷ�����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ر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⣬���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·����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У����ǵ���λһֱ�ڱ�Թ�����ʧ��֢�������ǰ�һ���ʡ�һ����ĸ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ʻ���ĸ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ǣ�����ȷʵ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һ��DZ��ʶ�ĵ�·����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֣���λ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ʹ�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һλ�dz���ʹ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ŵ�һλ��мһ�˵����ڡ���ʱ����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ʦ�Dz�֪������ֶ��е�ָ�ӣ�����ֹͣ˵���ѿ�ʼ�ľ��ӣ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ذ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Ѿ�˵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Ѿ�˵���Ĵ�ʵ�����ǵ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˵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ѡ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ڣ�������û���Գ���Ϊר����־ʱ��ƣ�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ھ��ǻ����ȥ��ijһ���£�����²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ͬ���й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Ż��ѻָ�ͷ�Ե���ȫ���ѡ������Դ����۾����ֲ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ø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ı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٣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磺“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Ź�棬ͬ�ҵ�һ�ο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ڿ������Ź�����ƣ������ڰ�����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Ū���ˣ����ڰͶ����ˡ�”����ȷʵ��һ�Ž���ͬһ�ֲ�Ʒ�Ĺ�档
����--------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Ϲ�Ҳ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֪�����Ϲ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ݣ���ᷨ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κβ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ʧ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ʧ���ñ����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λ·����Ůʿ�����ݵ����ǣ�û�б����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Ǿͻ��ø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Ϲ������类ĸ�������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ʺõ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һ��ʧȥ�˺������Ժ��еĺ��ӡ�——����ע��
�����ڲ��𰣣�1627—1704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̽�ʿ����˵�ң�֧�ַ���·��ʮ�ģ��Ĵ����Ծ�Ȩ�ۡ�
�����ڿ�ʼʱ�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��ϵķ����↑ʼ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ǣ���ͬ�ڻ谵�е��۾�һ�����ҵĶ���ܿ�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Ϊ���о�˵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ߣ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͵IJ���ԭ�������Եľ��£����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߷��Ķ������뵽��ʱ�ͻ���ʧ��Ҳ��ǡǡ�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ͷ�������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̸��ʱ˵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ּ�װ�ġ����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˷ܣ������˷ܻ�ʹ����˵��“���Ѿ��õ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Լ��IJ�”�������ǻ����̸����IJ�Ҳ���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о��ڴ˿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ǵ�������Ӧ���׳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糱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ӵ������׳������С�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з緢���ĺ���֢��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̸�۹�ȥ��Ҳ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ر�����û��ʧȥ���䣬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Ծ�������ķ�ʽ����û�б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л����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Щ�Ѿ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ǻ�ó��øе����⡣���ڻ������ǵ�ȥ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ʶ���Լ��ڻ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ּ����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飬����͡����з�Ĺ����ƻ�����ǧƪһ�ɵ������ظ�����“�����·��·���װ´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·��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Ķ�·˹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·��·��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·��·�����ʣ����ˣ���˹̩��·��·�Ŷ�ά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”ÿһ�Σ�“����”������䵽��Щ�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ڷ�Ĺ����ø���ľ�Ĺ���ӳ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ӳ��ص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˲�ȥ�μӸǶ�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˸��ľۻᣬ��Ϊ���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о�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з磬��ͣ�½Ų������ʺá����ǣ����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I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ļ�����ȴʹ�������˵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ͷ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ʵ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о��м����ʵķ������ѡ������ֱۻ�������Ͱ�Ŀ������Ͷ�����Ȱ����ң��·�Ҫ���Ƕ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ʲôҲû�ж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ͶԵ�·����˹����Ͷ������õ�Ŀ�⣬��Ŀ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Ƕ�����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ͬ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̬��ƽʱ��˲�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ƤЬ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о����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ʹ��ͷ�ŭ��ͬ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о�˵“����÷�£�”����ѯ�ʺ���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Щ�������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Ҳ�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ý�ȥ������Ǹ��˵����ϴ��ϣ����Ǿͻ��ڿ�ض���˵��“��ô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”�ⲻ��Ϊ�����𣬶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㣬�·𱻴��ŵ��˷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Խ��Խ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뿪�����ǣ������о�˵��“����û��ǻؼҡ�”
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һ�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Ȱ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·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شӿڴ����ͳ�һ���飬�Ҹе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顣�Ҵ����Ȱ��Ƕ���֪�о�����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ϸ�ڣ������е��ᷳ��“�Һܸ���ͬ��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”���Ȱ�����˵��“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ߵ�Բ�ι㳡��л��л�أ������о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˴��úܾ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̫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е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ֹ��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ɫ����ֻ�ô������ġ�”——�ر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Ѿ��ָ���”�һش����“����˵��ɥ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�dz��ѹ���”——“��ȷʵ����̱�����ֵز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ȫ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룬�������ڼ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кü����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ä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ƶ������кô���”——“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ٲ���һֱ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”——“��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յ�һ���ùݣ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����Ա�������Ҷ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ظе����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е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ѡ����ƣ����С��ͯ�����⣬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Ǹ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ҿɲ�֪�������ǣ������ð��ţ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м���IJɹ�����һ��——����ԭ���Ҷ���˵���£�������Ȼż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ã��Ҿ�ʲô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⣬��չʾ�Լ����յ����ܣ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൱������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У�——�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ּ���IJɹ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֪�����ǹ��ⰲ�ŵģ����Ժܿ�ͻ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߽��о��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‘ʲô��’——‘��ô��’�о��ش�˵��‘���ѵ��ǵ�һ�Σ�’��û���ž����˽�ȥ�����溦�¼��ˣ���Ϊ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ȷ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ͨ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Ҫ�죬�����о�Ū���ˣ���ʱ�о���ȫϹ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ȥϲ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ȴ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к���һ��”
�������˶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Ǹ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ÿ�춼Ҫ������֢�����ص㲻�������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Щ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¶���飬���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ڳ������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¶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ƽʱ�����Ŀ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¡���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Թ�¹��˵�ʧ�ܣ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¹��˵�һԱ�����Ժ���˵��“Ȼ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б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ܵģ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Ѿ�֤�������ܳԿ����͵������ǣ���֯����õ�Ҳ�����ǡ�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Ϳ�ŭ�ش���˵����“Xѫ����iji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Ϊ�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ǻش����‘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ǵĴ������ٲ����Һá�’”�������벹�䣬����·����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˼�벻���е�ʱ�̣���¶�������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ڳ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Ȱ����ǸǶ�â�ع������ˣ�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Щ���ʵ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Щ�Ƚ���Զ���ڷ��ֲ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Щ������ǣ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͡�“�������ģ�”���Ȱ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“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Ƿֿ����е������㿴�����Ѿ��跨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̸���ˡ��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û����뿪��һ��Ҳ�����ҵIJ��˶��Դ����Ƕ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ڿ��Ǹ����ӡ�”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Ƕ�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˸���Զ�ĵط������˳����ٴο�ʼ����ǰһ�������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ũ��֮һ���Ƶĵط�����ͼ�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ķֽ���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ͷ��ա���Ȼ���Ҵ��еó����й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۽��첢û��ʹ�Ҹе�ͬ����ʹ�ࡣ��Щ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䣬���ǣ�ÿ���Ҳ��ò��ı��Լ���ϰ�ߣ�����һ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µĵط����Ҿͻ�е�һ��ǿ�ҵ���Ȥ���ҽ���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Ȥ����ȥ��·�Ƕ�â�ط��˸�ۡ�μ�����ۻ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ǣ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Լ�ֻ�ܵõ����ĵ���Ȥ���ֺαذ����Ǿ�֮�����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룬������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дʱ�����䲻���в��ܵ�Ψһ����ȴ���в��ܵ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飬˿��Ҳû�и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ͼ���ҵļ�����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“�쾵��Ƭ”���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˹��ȡ�Ŀ쾵��Ƭ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Ӱ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д�ҹ�ȥ�����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Ŀ��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ڵ�ʱ�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Ҹе��ҵļ������Ͳ���ͬ������Ȳ�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Ƭ��֮���Һþ�û�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Ҫ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Ⱥ���ӣ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ĥʱ�⡣��û���κ����ɾܾ����ǵ�Ҫ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֤�ݱ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κ��ô�����ѧҲ�����ٸ��Ҵ����κ���Ȥ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ҵĹ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Ҳ���̫С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ʵ����ȷʵ���ҹ�ȥ��Ϊ��Ҫ�ٵĻ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“���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”�������ҵĿ����Ƕ�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ֲ����ɹ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У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٣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ʱ��һЩ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һ����ͬ��Ů�����ķ����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Ҷ��һ���꣬���Ҳ����м�����Ҳֻ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ӳ��IJ��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к����壬���ο���Ҫ�ӳ�����ڵ�ʱ�䡣����“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”�����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Ŀ�������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κ���Ȥ�صõ��ģ���Ȼ�Dz����ɹ�����Щ��Į�Ĺ۲��أ�
|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| �� 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껪�Ĺ��컶�ִ�� | �� ���ֵĿ���ʱ�� |
| �� ����ͼ��ݽ���Ѿ����ٶ�������껪ϵ�л� | 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껪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ں��տ��� |
|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