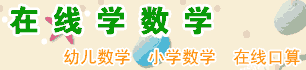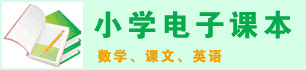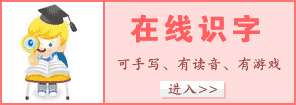���ݷ��ӡ������� ��ȸ��һ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ÿ���ط��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ط��ϵ�ѧУ�ṩ�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ɣ�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ѧ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ӵĵ��ݣ�Ҳ������ص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ӵĵ���
����ɣ�ǵĵ��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ȴ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Ķ����ܲ�������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“�����ң�������ô�߸ߵؾ�������”��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ȴ��δ�߸ߵ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ӥ�����˵ļ������ô�����š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˼�˵��“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ӡ�”���ǣ�ɣ�Ǿ�֪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ӡ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˴�ҵ�·�ӣ������ֶ��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ϻ�����ǽ�ϣ�ͨ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Ա�Լ�ȥ��ᣬȥ�Ҹо���
����ɣ�ǵ��ݵ�Ϸ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ɣ�Ǽ���һ����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ݡ�
����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ӣ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ġ�ũæ�ˣ���ͷ˵Ҫ�ľ���Ҫ��Ϸ�ݵ���ͷ��ͷ��ũ���ˣ���ͷ˵������û�£����и�Ϸ������Ҳ�ò������и�����úÿ���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ͷ˵��Ҫ�ô��߸����˵ģ����м���Ϸ���κ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ӻ�����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ص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ӣ��ڴ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ӻ����һ��ģ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���һ�㶼�������Сѧ��һ���ݷ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ǹ����ģ���ˣ�ʵ������ط��ϵ��ˣ���Ϸ��û����ʽ�ݳ�֮ǰ�������Ѱ�Ϸ�����ü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ǰ�ݺ�ռ�˴��ӣ����߸ɴ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ζ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ǿ��IJ���Ϸ�����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Ϸ���ȿ�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һ����Ա̨�ʱ����ˣ�ֻ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̨���أ���ͬ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
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ش����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ѧУ�ڣ�Ψһ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ѧû�й�ϵ��ס�������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ش����̡�ֻҪ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Ͼ���֪����֪���ˣ����ϾͰ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�Ź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ܴ�ͷ��β�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ҹ����ס�ش��ˣ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Ƕ����ۻ軨�ؿ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Щ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ӣ��ͻ�ŵ�����ɣ�ǵ����β�Զ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ĵ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”������ЦЦ����Ȼ��˵��“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���”Ҫ����˵��“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Ǹ����ˣ�ȴ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ϱ����”���˾��֣���Ҳ�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ص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ܿ��ó�һ̨Ϸ�������ڲ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˺ü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Ϸ��Ů��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Ĺ����ȸ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ȸ������ص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˵һ�����úÿ���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ϰ������Ϸ��Ļ�˵��“����”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ȸ����Ұ���ߣ��ܻ�Ѻܶ�Ŀ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ô����ɽ��¶ˮ���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ȴ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Ƕ�һվ������ٷ�Ʈ������Ҷ�Ļ�δ���ɵ���ͩ����ͤͤ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Ǻ��Ϳ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ȸ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ɤ�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ࡣ
����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˫�ִ����ڷ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ȸ����ţ�һ���ӣ���ˮ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Сľ����װ��һ�����⣬�Ǻ���һ��һ�ŵĶ������ޣ��ǵ��˶��뿴һ�ۣ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ӵģ�������ֻС����ǰ�ߣ���ǰ�ߣ���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ˮ�����Ϳ�����ͷ���Բ�ס�ؿ���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Ŀ�����һһ�������Լҵ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ϡ������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ˮ�ϵġ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յĺ÷羰��ǰ����һȺѼ�����߽��ˣ���֪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һȺѼ������һȺ�죻«έ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ֻ��ȸվ��«�����Ͻ���P �飬һ������ĺ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«έ��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ȸ�������죻ˮ��ͷ��վ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̿��Сϱ�������Ŷ��۾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˵���Ҳ��죬����Ҳ��ף�������Ͱ�ͷ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ĺ��⣻�����ⲻҪ����Сľ��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С����㷭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˼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û�е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һʱû��˼�ٳŴ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ˮ��Ư��Ư��ȥһ�����ˮ��Ȼ����ˣ��ƺƵ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һ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Ǹ�С������ǰ�߲�Զ��ˮ���ϣ�һɫ����ש��һɫ�����ߣ���һ��С���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֣�С���ϣ��Ҽ��̴�ð���̣���Ʈ����ˮ���ϣ���Ʈ�˱�����ɴ���㲻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µ�����һһ�������£����и����κ����ڴ�����……
����ɣ�ǵ���棬��ס��һ�����ˡ�
������ȸ�������˺ü��أ��·��Ǵ��ϵĹ��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СϷ����ֻ��һ�ѵ��Ӱ��ࡣ�����ӵ��ǽ�һ�֡�
����ɣɣ���ݵ�һ���˾��ǽ�һ�֡���һ�ֳ��úã����Ӵ��úã������úã����Ŀν��ú�……ɣɣ����Ľ�һ�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ü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ȱ���ˡ�
������һ�ֳ��úܸߣ����ߵò������ߵ��ȳơ�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ز���û�и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ǸߵóŲ�ס������Ͱѱ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̫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ˮ��ĻҺ��Ƶġ���һ��ֻ���˾��øߵúÿ�����һ�ֵ�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ţ�һ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ͷ������һ˿��ǻ�����У���һ˿��С����ζ�����ܷ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ߣ�¶�����ͷƤ�����ϱ����ϼ���һ���۾����Ͱ�һ�ɵ���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
������һ�ֵĵ������Ե�һƬ�ˡ�
������һ�ֵĵ���װ��һֻ����ѩ�IJ������ȡ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Ǻ����·��ؽ������ۺ÷ŵ��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Ű������㶵��ڽ�һ�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Ǹ��ˣ��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¡�һ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ǿ�������Ű��Ű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𣿽�һ���ڴ�����֮ǰ����Ҫϰ�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ָ�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ḧ�����£����Ӻ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谮��һֻè��һ��С�������Ӻ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ˮƽ�ġ���һ��˵�����Ӵ��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۾Ϳ����Ӻ��ˮƽ��ˮƽ����һ�ֵĵ��Ӻ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Ÿ�ˮƽ��ȥ���ԣ�ˮƽ�����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ˮ��϶���ƫ���е��ڵ��С���һ�ִ����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һ�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ôһ���߸����װ��˷��ˡ�����һ��˵��‘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վ��ȥ����”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ʲô�����ϡ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ӡ�
����ɣɣÿ�꿴����һ���⸱���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һƨ��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Ӿ��ǽ�һ�ָ��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ԣ��Լ����ģ���һ����Ȼ���õ���Ӧ�֡�
����ɣ�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ѵ��ݳ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֮�ͶԽ�һ�����ȸ˵��“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Ҹ��ط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ɡ�”
�������ϣ�ɣɣ�ڻ���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ߵIJݵ����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ˮ������ȸ���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ۣ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㱵�������ɣɣ�����彯һ�����ȸ�����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ǵ�Ӱ�ӡ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õ�����ɣɣ�����Ե����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š���ȸ�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¹������£��Եø������͡�ɣɣ�������ߣ������ؿ��ţ�ס�ļ�ֻ��Ӻ�����û������ˡ�
�����緭���ź�Ҷ���ְ����㴵���Ĵ�Ʈɢ����֧��δ�����ĺɻ�������ɫ����֧˶���ë�ʣ��ںڵ����š�ɣɣ�ܹ��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һ��ؿ��š�
����ҹɫ�µĵ�������̫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ͻ�Ծ��ȴ����Щ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ء�ҹԽ��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·�����ߵ��ˣ���Ҫվס��һ�ᣬ��һ�ᡣ��һ�ᣬ��һ�ᣬ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ɣɣ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ڿ���ɣɣ���룺��ʲô����Ϸ��ֻ�����¹������أ�
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Ͷ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“��”��ˮ�죬�ѽ�һ�ֵĵ�����ס�ˣ��Ѱ�ȸ�Ķ���Ҳ��ס�ˡ�
����ɣɣ�����ﳯ�Ǹ�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“���ᣡ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¿�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ڣ����Ž�����ɣ��˵��“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ǽ�����õ�һ��Ϸ�ˡ�”
�����ݳ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ҹ�����ݳ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ǰ���Ѵ���ȥ�ˣ������ݳ����˺ܶࡣ��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ѧ�IJٳ��ϡ���ͨ�������Сѧ�ٳ��ĸ���·�ϣ���δ�ڣ��˱�һ��һ�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ͷ��̫̫�������Ű�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룺�ٳ����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Ͽ��ɡ���ˣ����Ǵ��Ϳ����֣����ɵ����ţ����ţ����š������С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صط����նӵ��ݳ�ˮ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õģ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ݳ��ľ��ǽ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ص��ˣ���࣬�����˷�Բʮ��ص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һЩ�˼ҹ���һЩס��Զ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Ҫ�������Ͷ��һЩ���ӡ���ˣ����ݳ����磬�����Ͼ��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ŵ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ȥͦ׳�ۡ�
������ױ�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Ǵ��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Χ�ڴ����ſڿ���ױ��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Ϳ���˸�ɫ�Ͳʡ���Ա�Ǿʹ������£�һ�����ع��š����Ǹ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Ҫ�ģ�ɣ�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µؽ����Ǵ�ȥ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Ҫ��ɫ��ɣ�Ǿͺ����棬ױ���ò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Ǹ���Ա���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ϸ�ģ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µ��ˣ���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ѿ�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ࡣ
����ɣ�ǻ�ױ�Ż�ױ�ţ������Ͼ��ý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ʲô���飬ż��̧ͷ����һ�ۣ�һ�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һ�֣���ͻȻ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ȸ��û��ױ�ء����ʵ���“��ȸ�أ�”
����“��ȸ��û������”����һ�Դ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ֹ���һ����“��ô��ģ������ˡ�”�������ݳ�����Щʱ�䣬����Ȼȥ����Щ��Ա��ױ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ⲻ����ת���Ѿ���һ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ֱ������ݳ�ʱ���Ѳ�Զ�ˣ������ߵ�ɣ�����ߣ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“ɣ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û������”
����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ϸ��ױ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Ա��˵��“����”���Ͷ����Ǹ���Ա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‘������”����Ա˵��“�����ӣ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”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·�ˡ�
����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“��㡣”
����“����”�����Ӵ�����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Ա���ֶ��Լ�Χ�۵��ˣ���һ��Ͷ�֪���˰�ȸδ�����Ͱ�һ�仰�����ظ��ţ�“��ȸ��û�����ء�”�ֹ���һ�ᣬ�⻰�ʹ����˲ٳ��ϣ���ʶ����ʶ�Ķ���˵��“��ȸ��û�����ء�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ƺ�ͦ�ش�����Ҳ�е��е�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˷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ӹ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ɣ��˵��“��ȸ�����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”
����ɣ���ʣ�“Ϊʲô��”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Ӳ�֪Ϊʲô���˽�һ��һ�ۣ�ת���ش�ɣ�ǣ�“��֪��Ϊʲô��”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Աû��ױ��ɣ��˵��“�Լ���ױ�ɡ�”�ֶ������ӵľ��帺����˵��Ψʱ�ݳ�����ȥ��ȸ��һ�ˡ�”˵����ߣ�һ�仰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⣺“˭�����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ȸ���ܲ�����”
������յ���͵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“���”��ȼ���ţ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̨�յ�һƬ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ݳ�ʱ���С���̨�µ���һ�߿��ݳ���һ�߾������滥���ʣ�“��ȸ������”̨�����ԱҲ�ڻ����ʣ�“��ȸ������”
����ɣɣ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ڴ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ʱ���۾���ͨ���ٳ���·�ϱ졣�ü��أ���һ�ֲ�һ������Ӵ����ˣ��ҿ��Ǻ��࣬�����ĵ�ɣɣ�ú��ٽ���ЩС©��һһ��ס�ˡ�ɣ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øм��Ϳ佱��Ŀ�⿴�����ü��ء�
����Ļ�䣬�����ڿ�϶�X����ѯ�ʱ�����ʣ�“��ȸ����û�У�”
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Ŀ��ʼʱ�����ǵ�ע�����ͼ��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ϵ�����̫�á�
������Ա�ǿ�ʼ��Թ��ȸ��“�����ȸ������ݳ�Ҫ�ݲ���ȥ�ˡ�”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Ŀ����ȸ��δ�������Ǵ�“��ȸżȻ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ݳ�ʱ����”��һ���뷨���ƿ�ȥ�����ʣ�“��ȸΪʲôû������”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ԭ��ģ��㿪ʼ�˲²⣬��˼���ϲ���̨���ݳ��Ľ�Ŀ�ϡ��·����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ݳ�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ר���о�“��ȸΪʲôû����”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ȸ�DZ����ĸ��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�ʱ���²�ͱ�ü����ޱʣ���ʮ�־����ˡ�̨��һ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뿴��Ŀ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̫�����ˣ�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Щ��Ȥ�IJ²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ˣ���ʱ̨�ϵ��ݳ���ʵ������û��̫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̨ǰ̨�����Ա�����ż���“��ȸ��ô�������أ�”
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˴���˵��“��ȸ���ˣ�”
�������Ǻ����Dz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‘��——��ȸ����——”�����ǿ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ź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˶�ȥ��·�ϣ�̨�ϵ���Ա���ֶ�Ҳ��ͣס����·��——�¹��µ�·���տյ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“�Ķ��а�ȸ��”“û�а�ȸ��”“˭��˵�ģ�”һ�����ˣ�ȥ�Ķ����Ǹ���˵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Ŀ�������Ŀ�����Ǿ�����һ��СС�ij嶯��
����̨�ϵ��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̨�µ�����ʱ�Ȳ�ȥ���ȸ������ǿǿ�ؿ��ţ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Ա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ǡ��Ǹ�����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𣬺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Ƿ紵����Ҷ�죬����ȴ��Ϊ���Ǹ�����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Ҷ“ɳɳ”�졣ɣɣ�Ѻ�������ҡͷ���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н�һ�֣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��ɣ����Ӵ��ý��Ͱͣ���ʧ���յķ�ɡ���Ҳû�д�ǰһ�����Ӿ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ε����ӣ��Ե��е㽩Ӳ��
����һ��Ů��Ա���Ż�����һҡһ�Σ��紵�����Ƶ�����̨������һֱ�ߵ���̨�ڣ����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Ͼ�Ҫ����̨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Զ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Ҷ��Ʈ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ǰ�࣬ͻȻ˵��һ�䣺“�Dz��ǰ�ȸ��”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Ϸ��ͷ��һ��̨�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ȷ�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ţ�������·��һָ��“��ȸ��”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վ������Ťͷ��·�Ͽ���ֻ��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ȵ��߹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Ů�ӡ�
����“�ǰ�ȸ��”
����“���ǰ�ȸ��”
�������˾Ϳ��Ű�ȸ���Ų�æ���߹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ȸ�����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Լ�ؿ�������һ·�ߣ���һ·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ץһ��·�ߵ���֦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֧��ʲô�ġ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ð�ȸҲ���Dz�һ�㡣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·�ڣ���֪��˭�ɻ��˵��һ����“�ǰ�ȸ��”
�����ܶ��˸��Ż��ɣ�“�ǰ�ȸ��”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“���ܼҵĶ�Ѿ��”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˴�Ц����Ϊ�ܼҵĶ�Ѿ���Ǹ�������ë���Ĺ��һ��“������”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Ѿ�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ĵƹ��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ؿ������Ƕ�Ѿ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Ѿ����ô���˳���Ц���ܲ���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ȵ��߽��˺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̨���Ǹ�Ů��Ա����ͨ�죬����ͷ����̨�ߡ�������̨��ʱ����һֱ�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û�����ң���Ҳû�����ң���ǿ�Ը��š�
����̨�����˺�Ȼѧ���ղŵ�ǻ����“�Dz��ǰ�ȸ��”
�������˴�Ц��
����Ů��Աû���꣬�ߵøϽ�����̨�ܣ���Ҳû�п���̨��
����̨�µ�����Ӵ˱�ø����㲻���ԡ��ܶ��˲������ˡ�ɣ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ӡ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̨�Ϻ����Σ���֪���dz���̨�����Ǽ������̨�ϡ�
����̨�µ��˺���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ȸ���ɡ���ʵ�������м�Ĵ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ʶ��ȸ����̸���϶�ȸ��Ϸ���˽⡣ֻ����Ե�ʵؾ��ã�һ���а�ȸ����Ա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Ǽ�Ѱ�������顣������Խ��˵�Ű�ȸ����Խ���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Ϸ��ʵ���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ȸ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ȸ��Ҳ�͵���û�п���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ݱ���˶��ݳ���λ���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Ϸ�������ǵİ�ȸ��û�������ⲻ��ک��ô���ⲻ�������ǰ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ֵ��˵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ֵ��µ���˼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Ա��˵��“��Ҫ�����ˡ�”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ӵĸ�����˵��“ɣУ��û�������ݲ��ݣ�Ҫ�õ�����ͬ�⡣”
����“ɣУ����ô�����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أ�”�м�����Ա�ߵ�·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û������ɣ�ǡ�
����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˽У�“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ȸ��”
�����ܶ��˸��ź���“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ȸ��”
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Ա�Ǽ�ʹ���ݣ�ʵ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ˡ�
������Ա���ֶӶ������˺�̨��
����̨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
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վ��һ����ͩ���ĺ�Ӱ�һ����ɥ��
����ɣ�����ڻ�������Ա����æ����Χ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һ����“�����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”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ɢ�ˡ�
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һ��ʮ����Ҳû���Ű�ȸ��һ�пվ͵��ӱ��ϴ����ӡ���ȸ�ļҾ��ں��DZߵĴ�������룬��ȸ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ʲô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ͷ��β�ش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ֱ��ɣɣ���ã���ȸҲ�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Щ�����Ķ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վ���ӱ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ִ����ӣ���û��һ��֪����һ�ֵ�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ʦ�����Ӵ��úá�”���úܸ��ˣ��·��ǵ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Ǵ��ġ�
������һ�ִ�����ʱ��ɣɣ��վ���Լ�ˮ��ͷ�Ͽ�����ɣɣһֱ��û�п�����ȸ��Ӱ�ӡ���ȸ�·���Զ����ʧ�ˡ�
������һ�ֲ������ӵش��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ȸ����û�г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Ǹ������죬��һ��һ�����ȥ�˺ӱ��ϡ���һ�ֽ���ĵ��Ӵ��ñ������κ�ʱ�ã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ߡ�
�����ش����̼Ȳ�֪����һ�ִ����ӵ����⣬�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֡���ֻ�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ʦ���Ӵ�����࣬�Ͳ���ΡΡ�ض���һ��ˮ��“ЪЪ���ȿ�ˮ�ٴ���”
������һ�ֺܸ�л�ش�����һһ��һ�����ں�����л�ˣ�����ˮ�����¸����ӻ�������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ֱ�������ᷳ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ʦ���о�û��ʹ�ˡ�”
������һ�ֵĵ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ѽ�Ҫȼ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ذ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˫���뿪�ˡ�
����ɣɣͻȻ�ؿ�����ȸ���ӱ������ˡ�
������ȸ�����Ǹ����ӣ�ֻ�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Щ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ɣɣ����Ұ�ɣɣ�;�����ؼ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ࡣ��ȸ���ţ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ӯ�I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˫������ץ�ű��ŵ�����ǰ���Ǹ��ֺ��ֳ��ı��ӣ�һ��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ķ紵�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ɣ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ȸ�ߵ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۾����ղ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ǿ������¿���һ�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ѿ�����Ӱ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ڻ���û�п�����Ӱʱ������¶����Ȼ��ʧ�����ӡ�
������ȸ��Ȼ���ڰ��߶��һ�ᡣ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ӱ�ϴһϴ�ֵ����ӣ�����ʯ������ˮ�ߡ�
����ɣ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ֵ������ܡ�
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ЬҲ���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ڴ��ϡ�
����“����ʦ��”
����“ɣ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”
����“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”
����“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”
����“ȥ�ӱߣ�”
����“ȥ�ӱ߸���”
����“���ںӱ��ϡ�”
����“˭�ںӱ��ϣ�”
����“��ȸ��”
������һ�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ǽ��“Сɣɣ����Ҳ�Һ������ʦ����Ц��”���ţ�����һ��ľ����ѧ��Ϸ���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“��”
����“��ȸ����ںӱ��ϣ�”
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ɣɣһ�������ż��ı��飬��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“��һ�ᣬ���ͻ��ߵ��ġ�”
������һ�ֻ�æ���ӱ��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ɣɣ��ǰ���ͽ����ֲ���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ɣɣ˵��“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ȸ������ν�ġ�”���Ų�ȴ�DZ�ʲô�������ٻ��ţ��ߵúܿ졣
����ɣɣ���ں�ߡ�
������ɣɣ�������龰�ǣ���ȸ�ı�Ӱ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ʧ����ڣ�����ȸ�ĸ��װ���ȴ������˫�֣��Ѻ��õ��繣��ͣ�ںӱ��ϡ�
�����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ӱߴ����ӣ���Խ��Խû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�ɴ�Ͳ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ڴ����û�н����Ž��ײ�����ײ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Ͱ͵�����һ�ԡ�
������һ�ֵĿν�������ɣ���һ�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……��һ�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Ӷ�����ɡ�
������һ�ֱ���ر���˯����һ˯��Ҫ��Զ˯��ȥ�Ƶġ���һ����һ�ھ��ϴ�˯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Ͽ����dzٵ�����һ�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˯�߶����ף�ɤ�������˯�߶�˻�ơ�
����Ů��ʦ��櫶���˵��“����ʦ����Ī�Dz��ˣ�”
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Լ�Ҳ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ˣ�ȥ����ҽԺ���˼�顣�����û���κβ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ӵ�˱��ӣ����˯ȥ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һ�����ڣ���һƬ������ѧ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죬�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ܺã�ֻ�н�һ�ֵĿΣ���Ҳ�̫���⡣��һ�ֵĿ���Ȼû�кú�����ͷ�����ң�������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Ŀ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ġ��Ķ����Ļ��ʱ�䣬�����⻨�ʱ �䣬���⻨�ʱ�䣬���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ӣ��ӿ�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ġ�˵�ϿΣ��ͻ������룬˵�¿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֮�ʣ����ø�һ���䣬Ȼ��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“����Ŀξ��ϵ�������¿Σ�”�������䣬�����漴���𡣽�һ������⣬�����¿λ���ʮ���ӣ��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��ε���λͬ�ʣ���Ȼ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ǣ������ֱ�û�кú����ң�����ͣס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һ�ֲ�֪�����¿�ʱ�䵽���ж�Զ���뽲�¿Σ����¸տ��˸�ͷ���¿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룺���ˣ����ٵ�һ��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ȣ��¿�����Dz��졣
������ͬ��У��ʦ���ں����ɣ�ǣ�һ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ǿ���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ᣬ������ס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ʭ�ӣ���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ʼС��˵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Ƶ��ǣ���һ��Ҳ��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Щʲô����Ȼ˵����ôһ�仰����‘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һ�ᣬ���Ͼ�Ҫ�¿��ˡ�”
������У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Ů��ʦ�ﲻסЦ�ˡ���Ц����Ȼ�DZ�Ŭ�������˵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ƣ�Ҳɵ����Ц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ͨ�죬���ϳ������飬�������ϰ�ɿΡ��ɸյ���˵��“���ǰѿ��ķ�����һ��”ʱ������ȴ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磬�������Сѧ�д���У��ʦһ�ٷ����Է�ʱ��ɣ��Ц�����ſ��ˣ���ʼ��Ц�ò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а���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飬��Ϊ���̻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ѧ��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κ�һ��ѧУ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ң�ǰ���죬ɣ�ǻ�ר���ٿ���ȫ���ʦ���飬�ص�ǿ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⣺��ҵ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Ҫ�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ɾ�Ҫϴ�ɾ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ú����Ϳ�ģ�ûʲô�����ģ�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β��У���˺һ�Σ����°���ҵ��ȫ˺�ˣ������ٻ����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뵱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ù�ҹ……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ɣ�����ڸ������ſ�Ѳ�ӣ�������һƬɳɳɳ��˺ֽ�������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Ҷ�ӣ���ɣ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˷�����ʦ�Ǵ���һ���˿ˣ��Ϳ�ʼ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ȷʵ���ã���У����ʦ�Ƕ�˵��“�����Сѧ��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ɾ������˲��̿���”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ӣ���У��ʦ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û�����꼶�����ı����Ͷ�ɣ��˵��“ɣ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꼶�����ı���”
����ɣ�ǶԱ�У��һλ��ʦ˵��“ȥ���ʽ���ʦ�����꼶�����ı������Ķ��ˡ�”
����“����ʦ���ڡ�”
����ɣ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ܰ����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ȥ���ῴ����”
�����Ǽ������ᣬ������ʦҲ��Կ�ף��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ģ��ڽ�һ�ֵĴ�ͷ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ı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ǰᵽ�˰칫�ҡ�
������У��ʦһ�����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˸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ɣ��˵��“ɣУ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һ�°ɡ�”
����ɣ�ǿ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ֿ��˼�����Ȼ��һ�仰Ҳû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ı�������д��һ����Ϳ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ˮ������i�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ǣ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ˡ�
������λ��飬�����Сѧ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졣
����ɣ�ǽ���У��ʦ���ߺ��ڰ칫�ұ������ף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֣���ֱ����ͷ��”
������һ�ֵȵ����Ѻ����Ż�ѧУ��
����ɣ��һֱ���Լ��İ칫�ҵ��ţ�����һ�ֻ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߳��칫�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仰����“�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ʦ��������顣”˵��ؼ�ȥ�ˡ�
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˼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ǰ��֪дʲô������һҹû˯�����ڶ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ɣɣ���ܹ��صؽ�ɣɣ�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Ž���ɣɣ���ϣ�‘ɣ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Ž�����ȸ��”
����ɣɣ���ͷ��
����“���ĵġ�”
����“��֪����”
����“���ھ�ȥ��”
����ɣɣ���Ŵ������ɣɣ�߳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Լ��ǵ�Ӱ��ĵ��¹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ظС���ʥ�У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սս�����Ľ��ŸС�����·ʱ����̽ͷ̽�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¡�����ȫû�б�Ҫ����Ϊ��Χ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˭��ȥע�����أ�
�����ڲ���һ�ܵ�ʱ���ɣɣ���ڽ�һ�����ȸ֮�䴫�����ķ��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ٳ�һ���Ļᡣ
����ɣɣ�Դ���֮����³����˺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ŷ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ܴ�����ŷ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—һ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硣���ڽ�һ�����ȸ֮�����ش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ֿ��ŵĸо�������߽�������ռŵ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ֻ�۾�������ס���Ļ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ںڰ���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˶�װ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ɴ��µĺ��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˽⽯һ�����ȸ֮���ͨ�ž�����ʲô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Ը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š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֡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볡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Ⱥ�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˳��ڵ���Խ����⡣
����ɣ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쿴�������Ͻ�һ�����ȸ���¹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ã���һ�ֺͰ�ȸӦ����һ��——���Dz�Ӧ����һ���أ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ɣɣ��һ��ľ��ҡ���˺��DZߵ�һ�ô����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Ž�һ�֡�
�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ͣ�ڰ��ߡ�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з硣�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«έ�һΣ�����ˮ���ˣ�һ��һ�����Ĵ��ź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żȻ��һ����֪���Ƿ�ľ��ǣ��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żȻ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ҹ��ļ�į���Ͼ�Ҫ���ˡ�
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Ҳ��ɣɣ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ֽ��š�������ɣɣ��ǰ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ʦ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ɣɣһ��ƽ���Ķ����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ӣ����һ�Ҫ��ɣɣһ��ӡ�������ȸ֮�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ꡣ
����ɣɣ�����˽Ų������Ӵ���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ȸ���ˣ���ȸû��һ����ŵ����ӣ�����Ҫȥ��һ����Ҷ�֪�������顣�����˴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˫�ȴ����ڴ������ͬ����̬�Ľ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档
����ɣɣҡ�Ŵ�������ҹɫ����ǰ�С�ɣɣ������ˮ���С��һ�����˾���ʱ���ܳ�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ҡ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ϴ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ˮ���ˮ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봬�����ȳƵĺ���ҡ�����Ǻ�������ƨ�ɣ�һ��һ�ϣ���Ȼ�ѿ�ҡ���ܴ��ˮ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ڰ��죬ɣɣ��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˱�������ҡ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Ѷ������ú��н��࣬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�˭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ҡ�����Ͳ�ȥ�ں�����һһ������ֻ�뽫��ҡ�ÿ�һЩ������ô�����«έ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ʣ�“˭��ҡ����”
����ɣɣ���ش𡣽�һ�����ȸ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ش𡣴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·��˭Ҳ��ȥ���ᰶ�ϵ��ˡ�
������ׯ��ѧ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Զȥ�ˣ������ڽӽ���ӿڡ�
����“���ǿ���˵���ˡ�”ɣɣ�롣
�������ǽ�һ�����ȸ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ɣɣ�����ƣ�“�ò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أ�”
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ȸȴ���Dz�˵������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и¸�����ɣɣ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ҹ�е�ҰѼ�ӡ�ɣ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Ƕ�ҰѼ�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ط��ţ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Ӷ��ܻ���—ҰѼ������ôһ�������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˴�ӿڣ�ˮ���Ȼһ�¿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Ӷ��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ˮ���Ͼ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ɫ��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ɫ��·��ֱ����Զ����ͻȻ�ؾͶ��ˡ�ɣɣ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ɫ��·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Լ�ؿ������Ǹ�«έ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ˮ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Ϸ����һЩ�����㿪ʼ�ζ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ȸ���ɲ�˵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ɣɣ�룺Ҳ��֪������ʲô���ˣ����˵���Ϊ�ܹŹ֣������벻���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«έ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Ƭ�ܴ��«έ�����¹���һ���ʡ�
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˰���ɣ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°�ȸ�ģ�����ȸ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æ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˰��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ƺ�������Զ��«έ����һ��ų����ܳ�ʱ��վ���Ƕ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
����ɣɣ˵��“��һ���˾��߽�ȥ����Զ��Զ��”
������һ�ֺͰ�ȸһǰһ����ǰ�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ֻ�ͷ�ʣ�“ɣɣ�����أ�”
����ɣɣ˵��“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”
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ȸ������ǰ�ߡ�վ�ڴ��ϵ�ɣ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ţ��Ͳ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ҽ����ذ�����һ�𡣵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ǡ�ɣɣ�������ǵ���ӰҪ�Ȱ���i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«έԽ��Խ���ܣ�ֱ����ȫ���ڵ�ס�����ǡ�
����ɣ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ոɾ�����ˮϴˢ��һ�㡣�������Ǿ�ֹ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Ʈ���ġ����²��Ž�һ�ֺͰ�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أ�����վ���أ�������˵Щʲô��ɣɣ�²ⲻ�������Ͳ�ȥ�²��ˡ�����Ȼȥ����ա�����Ȼ�ؾ���һ���˶������Ŵ��ܹ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Լ���һ�衣����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Ƶ�����«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ʮ�µ�ҹ���´����š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ȸ��δ˵������ʹɣɣ���ź����ѵ�����Ϊ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ӵ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һֱû��ֹͣ��
����ɣɣ�ɵ��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㴬�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ģ������ڸ���һ�ֵĵ��Ӱ��ࡣ������ɣɣ���Եɵɵ�˯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罫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͵ؼ�����һ�£���˯�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ܿ���һ�ˣ�ֻ�����ˮ�����е㺦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ѭ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ŵĵ����߹�ȥ��
�����¹��£�ɣɣԶԶ�ؿ����˽�һ�ֺͰ�ȸ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õĻ����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ơ���ȸȴ�������Ƕ�����ȸ��û�п��Ž�һ�֣���˫�������°ͣ�����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š������յ�«���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·�ѽ�һ�����ȸ�����Χ����һ���λõ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ɣɣ����«έ�ˣ����ٳ�ǰ������ɳɳ�������˽�һ�����ȸ�����Ǻ�Ȼ��ʶ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̧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“Ŷ”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Ű�ȸ˵��“�첻���ˡ�”
����ľ���ص���ǰ�Ĵ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¹�������˯���ˡ�
����ɣɣ�䵱��һ����Ц�Ľ�ɫ�����˼�ɣɣԸ�⡣����˵“ɣɣ�ǽ�һ�ֵĵ�����Ա”��ɣɣ��ĸ��˵“ɣɣ�ǽ���ʦ��Ǯ�͵�һ�����ȵ�”��ɣɣ���ܱ�����ô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Ը�������¡�
����Ψһʹɣɣ�е��ź����ǣ���Щ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ͣ�����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͵��˽�һ�ֵĻ��ȸ�����ϡ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С���ܡ�����ЩС���ܣ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ǰ��һ�Σ�����ʧ�ˡ��ͷ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Ŀڴ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ǣ��ɻ��Ǻܿ��ֱ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ˡ�
����ɣ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ֺͰ�ȸһ�����˶��ٷ��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Խ��Խ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ͷ����Ҳ���Կ����𣿾���һ����ͷ���;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˺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ͷ����̣������ϷŹ�ɣɣ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졣
����ɣɣ���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߽�С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ɣɣ�;��ð�ȸ��Ӽ����߳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û�и��װ�����Ӱ�ӣ��ͻ��һ���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ɣɣ��ʼ���衣
������ȸ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ɣɣһ���š�
����ɣɣ���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Ÿ裬�����ò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Ǵ��ŵ������ں���Ĵ���
����ɣɣ����С��ͷɿ����ѧУ�ܡ�����ÿ�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Ž�����һ�֡���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ڽӹ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ӡ�
������һ�ֱ�ɣ�ǽ��ߣ������Ϲ���칫��Ʒȥ�ˡ�
����ɣɣ�е�ɨ�ˡ�
����ɣɣһ���ߣ�һ�ߴӻ����ͳ���ȸ���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š���ʲôҲû�п�����ֻ�ǿ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غ�Ӱ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ﵹ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Ц�ţ�‘ɣɣ������͵������ʦ���š�”
����ɣɣ˵��“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û�п���”
����“���뿴��”����˵��
����“�ҲŲ��뿴�ء�”ɣɣ�������·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
����ɣ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ӣ��Ӹ������ͳ�һ����ëδ��ȫ�����ĸ��ӣ�˫�ֽ�����һֻһֻ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У�һֱֻ�Ӿͷɵ��˷����ϣ���һֻȴ�ڷ�����֮��֪�������Ķ��䣬��Ȼ�λ����Ƶط��˺ü�Ȧ������䵽�˺ӱ��ϵIJݶ��ϡ�ɣ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δ�ܸ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˲ݶⶥ����ֻ���Ӽ���ɣɣ���Ͱ������ӣ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ɵ����ӣ�����û�зɣ�ֱ��ɣɣ���Ͼ�Ҫץס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һ�ij��ɵ��˷����ϡ�
����ɣɣ����û��ʲ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ڲݶⶥ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
������ݶ�ܸߣ�ɣɣһ���£�˭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ɣɣ���ڲݶⶥ�ϣ����쿴�ƿ���·�ļ�ֻ���˼ҵĸ��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Ƿ��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ó������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ţ� �����dz��õ����š���Ȼ����ʲôҲû���š���Խ��ʲôҲ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Խ�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ͷ���Ĵ����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ˣ��Ľ���סһ��Ż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ӱ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϶���һֻ�һ�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ͷ�����Ųݶⶥ�ϵ�ɣɣ��
����“�ҾͿ�һ�ۣ�ֻ��һ�ۣ�”���³���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ϵ���ĭ�����ؽ������ſڡ�
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“ѽ”�ؽ���һ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ɣɣ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˲ݶⶥ�ϡ���̧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Ų��ӵ���Ҳ���뿴����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ĭͿ��̫�࣬���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Ƭʪӡ������˳�ִӲݶ��ϰ���һ���ݣ��òݾ����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ֿ���һ����ֻ���ŷ�ڳ��£���ô����һ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ŵ��˳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ų��ɿ��ˡ����ɵ����Ӻ����أ���ǰһ��һ�ܣ�ÿһ�ܶ�������Ѹ�ݣ������Dz�ס�����߿��дܣ���ö��ڻ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ͱ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ĺڵ㡣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ڸ߿շdz����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紵������ƿ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ɣ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ؽ��Ŵ��ˡ����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ֽ��
����ɣɣ��Ҫȥ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̧ͷһ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Ȼ�ֻ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һ���վ�ڸղ��Ǹ�������֦���ϡ�
����ɣɣ�տ��˸���ͷ������ˢ��ͨ�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۾������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Ƥ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ǰ�ǵ���ɫ�ġ�
�����紵�����е���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졣
����ɣɣ���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ɣɣû��ȥ���ţ�ȴȥ����һ��֦ͷ�ϵ���ֻ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۾����ƺ�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ŵ����ݣ��ڴ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ɣɣ��һ�ͱ�һ���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Щ��˵�ö�����֡�������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͵����ԡ�ɣɣ�����ĸ��֡�ɣɣ������Щ���ӣ�����ͦ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ɣɣÿ���ڿ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Ϊд�ú����ľ��ӻ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Ὣ����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ɣɣ���ð�ȸ�����е�ÿһ�����ӣ����ǿ���ժ¼���ʼDZ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ò�̫�����Ƿ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ֿ���ժ¼���ʼDZ���ĵľ��ӡ�����ǰû�м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ӡ�������ô˵��ɣɣ������Щ����ȷʵͦ���ġ�ɣɣ�룺�D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д�ɵ��أ�
������ȸд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֡��Ÿɸɾ����ġ�
����ɣɣ���ֳ����ˡ�ɣɣ����һֱ����ɾ�����ˣ�ɣ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˺ںڵ���ָӡ����ʹɣ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ŷ��ڲݶ��ϣ���˫���õ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磬����һ�½��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˫��ȥ��ץ�ڿ���Ʈ�ŵ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ڲݶⶥ�Ϸ����ŵ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ǿǿ�ؽ������ŷ�ץס�ˣ�ѹס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ҳֽ���紵���ˡ�
������һҳ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С����ͷ���Ƥ��һֻ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Ⱥ�ȷ�Զ�ˡ�
����ɣɣſ���Ƕ����Ҷ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ĸ���ѹ�����⼸ҳֽ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۰Ͱ͵ؿ�������ֽ�ڿ���һ��һ�ε������Ʈ���š�
����֦ͷ�ϵ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Ʈ����ֽ�������ΪҲ��һֻ�ʹ�֦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ֽ�ڿ��з��Ϸ��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Կ��е���顣
������һҳ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ˣ������ӣ�һ���ỹû�����µ���˼��
����ɣɣһ�����۾���ס��һ��С�������ؽ�������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ֽ��һҳһҳ��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ֽԽ��Խ�ͣ�Խ��Խ�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Ʈȥ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Ǽ�ҳֽ��ֻ�Ǻ��ҵؽ����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˲ݶ⣬ֱ����ҳֽ��ȥ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ҳֽԽ�ǽӽ����棬����þ�ԽѸ�ݣ����Ƿɲ����ˡ�
����ɣɣ�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ʮ��Զ�ĵط�ʱ����ͻȻ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ѹ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ֱ�ص����˺ӱ��ϵ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ɣ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ƣ�ֻ������մ������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ֽ��һ����ɥ��
����ɣɣͻ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ŵ���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Ǽ�ҳֽ���˳�������æ�ؽ�������ͬ��һ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ֽһ�𣬶��ӵ��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ۺ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ˮ��Ʈ�ŵ�ֽ���Ͻ������˺ӱߣ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ﷸ���뷸���ֳ�һ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ɣɣ�ص����Լҵ�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ż��ϡ��Ǽ�ҳ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ǰƮ���š�����ʼ��֯���ԡ�Ȼ�����Ǽ�ҳֽ��Ʈ�������ţ���Ҳ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ͷʱ��ż�������˻�δ�ӵ����ŷ⡣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ֿ�����һֻ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֦���ϵ���ʱ�ĸ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ŷ�ʹ�����˶�������ʲôҲû�ж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“���Ǵ���Ѿ�ƯԶ�ˡ�”ɣɣ�롣���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·������ļ�ֻ���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Ƶ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˺ӱߡ�
�����Ǽ�ҳֽ��Ȼû��ƯԶ��ȴ��£������ͷ�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մ����ˮ��ֽ����ˮ������ôƯ��һ�ᣬ�Ѿ��ɸɾ����ˡ�ɣɣ�ͺܰûڣ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ˮ��ϴϴ��ɹ���˲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æ�ܵ�ˮ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Щֽ�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⡢��û���˵ĵط�����С�ĵؽ�����һҳһҳ�ذ��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��ʹ�����֦�ϣ�Ȼ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ţ������DZ�̫��ɹ�ɺ�ĨĨƽ��װ���ŷ���ȥ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ɣɣ�����˽Ų�������̽ͷ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ʣ�¼���Զ�ˡ�����æ����֦��ժ����Щֽ����ժ�Ĺ����У�ֽ����֦��ס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˺���ˡ�ɣɣ�±����տ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أ����Խ������ų�һ������ԶԶ���ӵ��˺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ܵ��˽�һ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ɣɣ��Ժ�ſ�վ��һ�¡�ɣɣ�����˽�һ�֣���û�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ĸ���ȥ��һ���룬ɣɣ����û�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ȸ���ţ�Ҳ�����ˡ�ɣɣû���뵽����ȸ������ţ��Ƿ��Ҫ�����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ڰ�����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ȷ�е����ۣ�“������ʺ���ӣ��ø��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”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ƽ�������ܲ��һ����ľ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ʣ������֮һ����Ķ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ǵ�תͷ�������λذ���ߡ������ž��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ˮ���ܵ���վ������ͷ�ϡ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и��˳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“���ô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”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ӽ���һ��Ҫ�߹������ţ�” ����ȥ���Ǹ���ľ����ر��ϻ����ߣ���Ϊ��һ���ߣ�һ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��ˮ���Ѷ�ľ�ܻ��ˡ���Ŭ�������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µ������ͣ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Ҳ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һ�����ֵ����˺�������ϰ������ߡ��Ŵ����Ǹ������ˣ�һЦ��˵����“�������”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Ѵ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ʧ�ܣ������գ������Ǹ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ӽ�ˮ�У�Ȼ��ס���ε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ڼ������ȸ�뽯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Ʋ��Ͻ�һ�֡������Ͱ�ȸ��ôһ��Ů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ϵ��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ȸ�����ϵ��˾��ǽ�һ�֡���ȸ�ߵ��Ķ����۾��ﶼ�н�һ�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“�Ǹ���һ�֣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ʲô�õģ�”
������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ͷ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ջ𣬾Ͱ�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ڵ��ϣ�“�������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���ģ�”
������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“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ô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ܱ�û���ŵ�ǿ��”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ⵣ��Ҫ���ȸ����Ϊ��ȸ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û���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ڰ�ȸ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ʱ�����ܵ�����ȥ�ˣ�����һֱ�Ǹ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ȸ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ţ����Ų��ӣ���һ��һ�ʵس鶯�ţ�վ���Ƕ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ף���ȸ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ı��Լ��Ŀ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˸���ȸ���Ҹ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ܰѰ�ȸ������һ�֡��ھ���ʤ���翴���˰�ȸ����Ѱ�ȸ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έ����έ�����ϵ����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Ĺ�έ����ʤ֪���˰�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˵��“���Ǻ��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档”�������ð�ȸ���Ǹ���έ���档��ȸû�г�������ɲ�����έ����ȸ�ƺ�Ҳ���Ķ�������έ����ȸû�м���ؾ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ý�һ�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Ǿ�д���Ƿ��ţ��ʽ�һ����ô�죬��Լ�˽�һ���ڴ��Ĵ�ĥ���Լ��档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ʱ�䣬��ȸװ�ŵ��ԼҲ˵ظɻ�����ӣ�����һֻ����ȥ�˴�ĥ���ԡ�
����û���յ��ŵĽ�һ�֣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ȸ��վ�ڻƻ�ķ��еȽ�һ�֣�һֱ�ȵ���ڡ����е㺦���ˣ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ߣ�·�Ͼ����˽�һ�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ôҪ�����£���Ҳ�ҵ�����ȸ�뵽���ڹ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ִ�δʧ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ÿ�ζ������ȵ������ͻ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ӼǴ��ˡ��ǻƻ裬��һ��϶�û�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Ļƻ裬�����ҿ϶��ˡ���ˣ��ڶ���ƻ裬��ȸ�������˴�ĥ���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ذ�ȸ����ԭ���ˣ����Ų��ں��أ���ȸһ·�Ͼ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Ҳ���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ͼ���έ���ص��ң�����Ķ���˵��“�������Ҽ���έ���Ҽ���”
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һֱ�Ȳ�����ȸ���ţ��ֻ̻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ӱ��ϴ����ӡ�
������ȸ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ȸ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Ѱ������۾������ӱ���ȥ����һ�֡���ȸ�Ѽ�����έ�ˡ���ȸ������έ֮����һ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ĸо������ƺ��е��ڼ���έ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ɣ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ţ�ʵ����ֻ���˼����֡����룺������϶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£��Ұ����ǵ��µ����ˡ�һ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Ǹ��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ӣ����͵���ͷȥ����һ�ֽ���ʱ���IJ������ˡ�ɣɣ���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��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Ǽ�ҳֽ�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ط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ɣɣ��Ӱ�ȸ�Ƕ��ٵȵ�һ���š����죬���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˸衣��һ���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ǽ�ϻ��ŵ���һ�߳�������ͷ������β���ִ���β������ͷ���ߵ���ȸ���ſ�ʱ���Ͱ������Ŵ��˳�����ȴ�ܲ�����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ǰ�ȸ˯��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˿� ǽ�ϱ������µ�һ����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ijɴ�У�
����һ���ǣ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ƿ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ƿ©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ڶ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ڶ��㣬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⣬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죡
�����찥�죬
�����ذ��أ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ݳ�¡�����أ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ع������Ի磬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Ѽ�ӻ�Ȧ�̣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վ�ڰ�ȸ���ſڽл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ȸҲû������“��ȸ�㣬�D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ʦ�ˣ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”���ʹ���ͷ���뿪�˰�ȸ���ſ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ϣ�ɣɣ�ƿ��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ţ�˵��“�����ȸ�������һ ���ţ��Ұ���Ū���ˣ��Ͱ�������……”
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“��ѽ”��һ����˫�ֱ�ס�Դ����͵�ת��һȦ��Ȼ����ͨ���Լ��ŵ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ش��˼��´��壬����˫�Ż��ཫ���ϵ�ƤЬһһ���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ϣ�“�ҵ�ɣɣ����”
����ɣɣ��ֱ��վ���ſڡ�
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ͷ������ɣɣ��Ц��һ�¡�
����ɣɣ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û���߶�Զ����һ�ֽ�����ס�ˣ�“ɣɣ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ҡ�”
������ɣɣ˫�ֽӹ���һ����д����һ���ţ������ױ���һ�ָ�����ζ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һֱ�̻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ظ�����У�ſ���ȥ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ȸ�ҵĴ����Ѿ������ˡ�ɣɣ��ǰ�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ݣ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ȸ����Ҫ�в����ı��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͵���ȸ���ϡ�������ȷʵ�ƿ�ʩ�������ÿ��š������ŵĿ϶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ǰ�ȸ����ȸס�����ݣ�����ס�����ݣ��ߵ���ȸ��ǰȥ�����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ǰ�ݡ������ϼ�����ȸ����ֱ�Dz����ܵ����顣ɣɣʧ����վ�ں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ɣɣ�߳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˴���DZߵ������Сѧ�����Һܿ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Ӱ����һ���ڵȴ������ŵ���Ϣ��
����ɣɣ��ת���߽������ӡ�
����ɣɣ�����˰�ǽ���ִӰ�ǽ�������˰�ȸ�ҵķ����ϡ���ſ���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ȿ�����һֻ�����밵��С���ƹ���ľ���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Ϳ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˯�Ű�������Ъ��һ����ˮţ��һ�����䣬������ţ˩����߱���͵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ط��ϵ������˼�һ������ţ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˿̣������Ѿ���һ���ϴ���˯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ˮţȴ����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سԲݣ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ڻ谵�����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⡣
����ɣɣ���Ű���ģ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ף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ķ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ɣɣ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ͷ�������촰��Ȼ��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ÿ������ڽ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촰������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“ŶӴ����©���ˣ�”ɣɣ�����Ű�����“��”���˵�ʱ������ӣ������ݼ���ɵЦ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ɣɣ����û�а취��ֻ�ô��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˫�ŸմӰ�ǽ���£�һ�Ӵ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Ȼ�ɸղ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ͷ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ת�ţ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˼ҵ��ſڷ�����һ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ӱ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ˮ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ݼ��ϡ���ſ���촰�ڣ���ϸ�۲��˰������϶����Ѿ�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ز������촰��ˮţ�������촰�µ�λ���ϡ������ݼ���һЦ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б��ˮ����ˮ�Ӻ������˳������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ˮ���ڵ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ž�������졣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˶����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ž����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æ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·���δ���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˴�������һֻ�������˵Ĵ�ľ����˶��ľͰ���͵���ţ�ĸ���ȥ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ˮţ���еؽ��ݲ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ص���һ�ᣬ��δ�ӵ���ţ����һ��“����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ϴ�ȥ�ˡ�
����ɣɣ����һ�ᣬ�ֿ�ʼ���µ�ˮ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δů�����ӵİ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“������”��ֻ���ָϽ��´�������ľͰȥ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ý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ȣ�δ�ȵ�һ�Σ����ջ�����ľͰ����ţƨ���Ϻ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ƣ�“�����ģ�”�ϴ�ȥ�ˡ�
����ɣ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ú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Ȱ�������ֿ��Ժ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ֿ�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—ɣɣ��ʱ�ĸ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ܴ��Ǵ������ʱ�ܿڵ�ˮ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ţ������˵�ţ�“�ҿ������ҿ�����……”
����ţ����ֻ���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ֵش������˴�������ţ����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ߣ�“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㣡”
����ɣ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ݼ��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֨ѽһ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һ�ᣬ�Ϳ�������ǣ��ţ�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Ӻ����ԼҵĴ�ݶ�ǣȥ——���ǰ���˩ţ�ĵط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ţ��Զ�ˡ�
����ɣ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ܽ��˰�ȸ�ң������˰�ȸ���š�
������ȸ��Ȼû˯�������ţ�����ɣɣ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“ɣɣ�����㣿����ô�����ģ�”
����ɣɣʲôҲ��˵�����Ŵӻ����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ȸ���ϣ�ת�����ܡ�
����ɣɣ�������ӣ�һ·���ҽк����ֵúü����˴�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ʣ�“˭�ҵ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溰ʲô��”
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ȸ�ּ����ˡ���ȸ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ȸ�뽯һ��֮�䣬�ƺ��е����֡���ȸҲ˵����ԭ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һ�죬��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ص��˾�װ��ȥ��ȸ�ҽ趫����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έ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Ǿ�����ͷ���ͷ˵��“��ȸ�������Ǹ��еģ������ӳ��ò�����”
������ȸ����û��¶�棬�ʹ����Լ��ķ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έ�ڰ�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˾˾˼ҡ��ھ˾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ͻ�����ȥ�ˡ�
������ȸȥ������ѩ���࣬�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˹�έ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έ˵��“ȥ���Ƕ������ɣ�”
������ȸ��ԥ��һ�£�˵��“�ðɡ�”
������Ҫ�ź���ʱ����һ�ִ�ɣɣ���нӹ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š�������о�����ʲô���Ͱ��Ź����ˡ�ɣ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·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ſ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ǹ��š�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ɣɣ�ſ�����һ�ֽ��Ŵ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ſ��ϣ�˫Ŀ������ɫ�����ڲ���һ��Ĺ�����ͱ���㲲�����ɣ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ؾ��ã���һ�ֵ������и��˵���ۡ�
����ɣɣ��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ʲô�£���ɣɣҲ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˸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˺��٣���һ�־ͻؼ��ˣ�һȥ�ü�ʮ�죬Ҳû�е�ѧУ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ʮ���죬ɣɣȥ��Ұ���Ҹ��ӣ�ԶԶ�ؿ������ӱ��ϣ���ȸ����һ���е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ǰ�ߡ���ȸ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ɫ�Ľ����ް���ͷ����һ���ʺ��ͷ�����ھ�ɫ�����Ķ�������˾���ʮ����ů����ȸ�ϵ���ͷ��һ���ߣ�һ�߲�ʱ������ȥץһ�½�Ƶ�«έҶ��ɣɣ���ã���ȸ�ı�Ӱ����ȸ��·�����ӣ�������ĺÿ���ɣɣ֪�����Ǹ��еĽй�έ����έ��Ȼû�н�һ�ָ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˱�ֱ���Ե�ʮ�ֵ�Ӣ����һͷ�ĺڷ����ں��ϴ����ķ���Ʈ���š�
����ɣɣû�����Ҹ��ӣ��ͻؼ��ˡ�
������ѧ�ĵڶ��죬��ȸ��һ���ɸɾ����I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ɣɣ���ϣ�“ɣ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ǽ�������”ɣɣ���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籧��һ�����ص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Ŵ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ó������˿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ú�ɫ��ë�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š�����У����ת�˰��죬�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֡�
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һ����ƽ�������ӣ���ɣɣ����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“лл�㣬ɣɣ��”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죬��һ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ɣɣ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Ǹ�ε����ӣ�“ɣɣ�������鷳����һ�ˡ�”
����ɣɣ�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����涼�ǰ�ȸ���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Ʈ��ϸѩ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վ�ڻ������Щ��ע����ʫ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˼���ţ�һ��һ���Ͷ���˻��
����ɣɣ���뽯һ�ֺܽ��ĵط�վ�š�������ֽ����ѩ��һ����裬����ڽ�һ�ֺ�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߸ߵ���Ӱҡ���š�
|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| 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ݷ��ӡ��ɶ�ͯ��ѧ���� | �� ��ͯ�硶��ֻС�����ڳ�СѼ�糡���� |
| �� ���ݷ��ӡ� | �� ���ݷ��ӡ� |
|
|